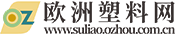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有什么共同点?如果爱玛·包法利最后解决了破产危机,她是否可以避免悲剧的结局?为什么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对冤家?英玛·伯格曼为何认为沉默是缓解心灵痛苦的方式?近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最新修订的散文与文学评论集《小说的十字路口》,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述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
 【资料图】
【资料图】
《小说的十字路口》收录了格非对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城堡》《红楼梦》等中外名家经典的分析。全书共分为三辑,收录了他的文化随笔、读书笔记与文学评论,其中既有对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文学名家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对英玛·伯格曼、门德尔松等艺术大师的作品鉴赏,每一篇都蕴含了他丰富的阅读、写作及授课经验,文笔犀利,见解独到。
《小说的十字路口》
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指南
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格非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30多年前,格非就以他先锋派作家的身份在国内文坛和读者圈内广受赞誉,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中短篇小说《迷舟》《相遇》《隐身衣》,专著《文学的邀约》《雪隐鹭鸶》等等,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获2015年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获2016年茅盾文学奖。同时,他还是清华大学中文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说小说家的身份为格非讲授文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艺术手段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作为作品呈现出来,体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思考和与时俱进的分析能力,那么作为教授的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更是天然充满“传道授业解惑”的柔和的体谅,少了高高在上的偏激的审视。
在分析《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时,格非认为读者有时容易陷入对主角“存在意义”的苛求,仿佛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如果不是生来完美的,就必须是为讽刺而生的:“有人说,福楼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就是为了批判爱玛身上的浪漫主义,批判她的不合时宜,她的任性和堕落。他们甚至得出结论,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彻底抛弃浪漫和幻想,脚踏实地地生活。”而他本人对爱玛“浪漫的梦幻”破灭的解读,在结合了社会实际的同时,给读者指明了另一种阅读的逻辑,理性和客观并非只有“批判”这一种表现形式,思考本身可以是平和甚至悲悯的:“……如果说作者对爱玛有一点点指责或哀叹,那也仅仅在于,在作者看来,爱玛对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当她在外省农场的阁楼上贪婪地阅读爱情小说的时候,她身处的法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浪漫’产生的土壤和气候都已消失殆尽。爱玛身上的‘浪漫’对于作者来说,犹如一根探测器。作者试图用它来衡量一下社会的庸俗、残酷程度。”
这样类授课的文学分析对于新时期的读者来说也应当极具启发意义,教授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在格非身上近乎完美地融合,就像他自己在《写作的恩惠》中所写:“我想,除了写作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诱人的职业,那就是在大学任教。现在,我同时兼有这两项职业,不仅心满意足,而且简直有些喜出望外。”
文学创作者的经验之谈
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格非也分享了他在多年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
他认为作者和读者作为文学作品创作和接收的两端,最理想的关系应当是在作品中彼此寻找。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躲猫猫,作者躲起来,设置重重机关、驿站甚至彩蛋,然后等待最终被读者找到;而阅读则是读者不断通关寻找作者的过程。在这种双向奔赴中建立起某种美学上的认同,这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而这种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不公开透明的,实际上受作家控制的部分是有限的,因此文学创作过程本身极具“主观性”。
首先,作家很大程度上无法挑选自己的读者,更无法控制读者对于一部作品的理解,阅读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都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影响。
其次是在作家自身的创作过程中,开始可能只需要一个灵感、一个随机的人物,但当行文渐进,故事的内容越发复杂饱满,作家设置的所有人物、所有线索都已经决定了,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必须遵循既定逻辑,从而强烈地牵制住作家,让作家不能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创作者再赋予人物的语言、行为已经不再完全出自“创造”,而是跟随故事自身的发展轨迹。
在书中,格非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智慧。相反,小说自身的智慧一直在引导和教育着作家……很多作家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价值的奴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