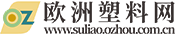九年前,我在戚城东郊监狱还只是一个没有职称的普通小狱警,因为人员紧张,我常常白天做训导,晚上则如同电影里演的那般,巡视犯人们的按时睡觉情况。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监狱里十几个罪大恶极的犯人陆续被转到省城里的监狱,顿时感觉监狱里人少了很多,于是我开始自觉地偷懒,不再按规矩检查每一个监舍,而是像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如果听到了些许人的响动,则会跟着同班的指导员对着那声音所在处训斥一通。说实话,长期待在这种地方内心会有强烈的焦灼感,这里太压抑了,每个人都像从水中捞出来的鱼,啜泣着泡泡活在虚妄之中。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好在半个月交一次班,每当走出监狱大门时,我感觉自己就如同一个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囚犯终于熬出了狱,身体里的腮又重新接触到了清凉的水,自己又重新成为了幸福世界的一分子。11月份的下半月,我重新回到监狱上班,收拾衣柜时,监区长来到我的寝室和我说两个小时前又有几个犯人被带走了,让我带人去做些记录,做完记录找到管保洁的让他们把监舍清扫干净。
果然故事的开头就是一件小事罢了,在县政府的办公室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如是想到!
与窗外铺满杂叶的池塘比,那总计有八个床铺的监舍看起来整洁如新。犯人们此时还在参加室外活动,有可能在跑步,也有可能是在打排球。我找到那几个人的床铺,他们的床铺在整个寝室中稍显得有些突兀,有些被子乱糟糟的,我心里喊着这些人到哪都是个祸害。
有一个床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把同来的王城叫过来看,这囚犯床上被子的下层都被撕碎了,布条像垂落的柳叶。王城说这种情况要向领导反映,这是明显的心理不健康。然后我们继续核对离监人员,发现这布条床所属的人就是离监人员之一。王城心里发急,他说要赶快向政委汇报,让政委及时通知省城的监狱。我点点头,让他先去报告,自己留下来清查最后的人数。
清查完毕,我又坐到了这柳叶床上,忽然发现这床的床脚似乎有些高,我把床垫拨开,发现床板上有着一本书《理想国》,书的扉页上有“戚城东郊监狱图书室”的红印盖章,书旁有着几块木炭,木炭的尖端被磨得像个铅笔芯一样。我知道这样的物品要上交监区,但在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里我的好奇心还未泯灭,我想提前审视一番也是训导员的任务范畴。
书的印刷内容没有什么奇怪的,开篇就是“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块儿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可怪的是,每一面都有木炭写的小字,这些字覆盖在印刷的宋体之上,小字扭七拐八的很难辨别,我只能耐着性子来看。
我就要死了,脑壳瘪瘪的,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土豆。这颗头颅现在也就只有鼻子、嘴巴和半只眼睛能艰难运行了,那些年轻人手中的酒瓶从半空向我的脑袋砸下去后我就注定成了个半死不活的人。在黑夜的一角,当南门兜的两个巡夜交警把我从花坛里拉出来时说:“这还是个人吗?”可我还活着,在轻弱的喘息声中,我还残留着一丝不太清醒的意识,我支支吾吾地喊:“看看许直叔,他,那几个人。”
我指的是和我一起从江西老家来到福州城的那个大我14岁、住我家隔壁的可怜的苦命人,同时还有那几个欺负我们的孩子。医生在看到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后,发着牢骚说:“这还要救?”我看到了他的脸,聚光灯下他的脸红红的,然后便听到了一阵橡胶手套撕扯的声音,再后来我就被钻心的疼弄得昏迷了过去。
这真是奇异,许直叔想死却没死成,我想活却最终要去受死。
就这么等死的时候,村里的母亲来看我了,她流着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穿过了那些太平天国的造反派都不敢穿过的武夷山岭来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她对我说,我的老父亲下田的时候听到了村支书说我杀人的消息,据说他当时愣了愣,头一仰就倒在水稻田里死掉了。我的母亲强忍哀痛,隔着玻璃窗,问我过年的时候能不能回家,我点点头——看见她身上那两件单薄的破布衣裳后便像是鞠躬一般郑重地点了点头。
已经到了深秋,上午的风已经变凉了,再有一个月我就要在北京与这个世界说告别了。
今年元宵还没过,许直叔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外地打工。那时屋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父母亲同坐在一个板凳上,满脸疑惑地盯着他们那蹲在椅子旁的弟弟,而我则站在门口听门外的瓦与雨之间有关战争的呐喊。
我父亲忽然起身说:“许愣,嗯搞西哩?”许直叔也踉跄地站了起来,对我父亲说:“哥,我要让兰妮读书,九月份就要去,嗯要给她挣学费。”半响沉默,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觉得他的弟弟需要砍点柴消消力气,好能够本分一些。
而许直叔则把嘴唇闭得紧紧的,抿成一条线。我抬起脚想进屋了,而他则猛地侧过头骂我道:“你叔我都敢出去闯,你咋像个孙子一样,都28了,窝到你爸后面哪个谁会跟你?”
我有些惊愕,我没有想到许直叔会说这样的话,同时他一直刻意不和我们说土话,尽管那调子还是乡里人的样子有些别扭,但这依旧使我感受到了他出走的决心,同时他的话也像一个炮仗炸响了我,让我有些站立不安。他接着说:“镇上王六说福建打工,一天能有六十块,我出去几个月,搞点钱够给我妮儿上两年学,那样就能够不像她妈一样。”然后他又深吸了口气对我说:“都看出来了,你小子想要张石头他家的女儿,但你莫钱,人家跟你?”
许直叔让我今天晚上去他家,也就是那个破平房里和他谈外出务工的事情。
吃完饭后我坐在那条我父母坐过的板凳上想着许直叔,我有些紧张,他大我14岁,在我20岁的时候结了婚,一年不到他就有了女儿。前年大年初一,他老婆用家里的一根扁担和两个萝子将家里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挑走了,然后初二醒来的许直叔发现本就破烂的家里就只剩下他和女儿了。那些天他站在村口呼天喊地,然后去县城西郊的庙里拜神,可就算是这样的折腾他的老婆也依旧没有回来。今年春节前,他把兰妹放在我家然后就去到镇上待了几天,回来后便和我父母说他看到了新的天和新的地。
晚上九点多,我走进了许直叔破败不堪的小房子,这里曾经是我家的猪舍,许直叔在变卖家产当做了香火钱后就带着他女儿住到了这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生怕把这破木门弄倒,接着兰妹把我领了进来。烛光的残影下,我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我想这样的衣服连乞丐都不会要的。
许直叔让兰妹去到屋外,接着就和我说起去福建打工的事。我攥紧双手听着,那60块一天的工资的确让我神往,我想60一天,我干个一年就有大钱了,张石头家的张舒就能嫁给我了。五天后我就和许直叔来到了福州城,兰妹则托给了我的父母,临走前许直叔向他哥嫂磕了几个头,然后带着我决绝地走了。
福州很大,非常的大,同时这里人很多,刚出火车站时,四围的电子亮屏晃得我睁不开眼。按照镇上王六的说法,我们需要直奔福州晋安的王庄在那落脚,然后随便找个厂就能发财。
我和许直叔一人拖着一个饲料袋,从火车站出来后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路上没有人肯给我们指路,我透过路边的积水看到自己的脸——黑得吓人,并与干净整洁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还好最后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给我们指了路,这使我想起自己读书的样子,想起自己曾经也戴着红领巾上学。后来父亲老了,让我回家,那时我想自己已经让父母供到了初二了,该回去帮父母好好照顾那几块地了。
看到第四卷时,我觉得犯人们可能都要回来了,我便将书和木炭装进公文袋中带回了寝室。整个晚上我神经紧绷,状态就如同学生在课堂上偷看小人书一般。我去食堂匆匆忙忙地打了一份饭,晚上心不在焉地查完了舍,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我生怕同寝的王民繁看出我的异样,便假装无意地说:“民繁啊,我今天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有些意思,我就自己点个台灯看书了,不会影响到你吧?”
“陈哥,你这样说就见外了,你直接点屋子里的灯看,我睡得着。你这次借了啥书啊,上次的是《死魂灵》,这次又是啥?”
“这次的是《理想国》。”说完我手发抖地抓着书腰把书的封面给他看,他在床上向下瞥了一眼,然后说些明天工作的事情就睡着了。我一听到呼噜声就赶紧看起这些字来。
穿过最后一个街角我们到了王庄,一个深红色的匾额上写着“王庄X所”几个字,第三个字只剩下一撇,像断了杆的拖把。不需要过多言语,我们走进了一户人家,说是外地来的,那胖女人就直接把我们带上了楼。
这是一间不到50平的小屋,里面有一张床,床头有一个茶几,床的对面有一个没插着电线的电视机。看到电视机我就和许直叔说就这个了吧,许直叔和她谈好,一个月270元,水电另算。
我急急忙忙地把电线插上打开了电视,里面的内容是彩色的,那些广告里的糖果亮晃晃地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想让许直叔也来看,可他却骂我没出息,他说要出去买点吃的回来,我有些怯懦地楞在那,仰起头望着他走出去。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工业园区内,这里的工作很累,我和许直叔在同一条生产线,还没到一星期我就受不了了,我对许直叔说:“种田比这个要自在多了。”让我奇怪的是,这次他没有骂我,他耐心地和我说:“吃得苦中苦,我们这些乡下家伙才能有点人样。”许直叔的普通话已经好很多了,如果不仔细听的话根本就听不到乡土味。
许直叔不仅在精神上鼓励我,他还帮我分担工作。按照规定每个人每天需要装配好一万五千个瓶子,那装满酱油的瓶子味道十分的难闻,有一次晚上十点多回出租房的时候我在路上上吐下泻,胃里全是酸味。之后许直叔就每天帮我解决三千个,工作时我偷偷看他的脸,脸上有着我不能理解的兴奋与自豪。
干到第四十多天时,工厂发工钱了,按照之前谈好的,我和许直叔全月无休可以得到二千一百多元。领工资那天,高个子的监工把两千多元钱连同我们压在那的身份证都发给了我们,可当我们领完钱后发现,那些个没有修满工的人居然得到了三千五百元。
一开始许直叔还和我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工资涨得挺快,等到所有人的工资都发完后,许直叔便急忙走向前对监工说:“领导好,领导好!”
那个高个子瞥了他一眼说:“怎么了?”
“领导,咱们厂子真不错,就一个多月,工资就涨到三千多了,您看?”
这时很多准备走的人都停了下来,他们很奇怪这个平时不爱和人搭话的家伙跑上去干什么。我也很疑惑,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突然那个监工对他大喝一声“滚”。我看到许直叔弯下的腰猛地直了起来,他也大喊道:“怎么的,‘人人平等’,道路两旁可都写着。”
“你给我滚,你个土猪,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也不看看这里是哪,给你两千也是老子发慈悲,像你这样的土猪本就不该给钱。”
我看到许直叔眼里带着怒气,我感觉得到他在克制自己的怒火,我冲上前来拉他的胳膊,可当我手一碰到他胳膊,他就立马将胳膊甩开,转而挥起拳头向监工砸去。
许直叔和那个高个扭打在了一起,二人都倒下了地,旁边的人都冷眼看着他们,也如此这般看着我。许直叔虽也倒了地,但很明显他正占据着上风,同时当他的拳头挥到那个监工的头上时我心中觉得无比畅快。
两分多钟后,几个保安把许直叔抓了起来,我这时猛地向前一冲,将那架着许直叔左右手的两人撞开,然后拉起许直叔就向外跑。
我们着急地跑回了出租屋,瘫坐在地上时,我问我们该逃吗?他反问我逃去哪?
半夜我们的门被敲响,房主用闽南语夹杂着普通话让我们起来,说有人来了。我和许直叔从那张床上惊醒,许直叔抵住门问是谁,这时又响起了一个令我熟悉的声音,是厂子里同班的王叔。
我上前打开门,叫了一声来人“王叔”,他点了点头说委屈你们了。这时许直叔还保持着警惕问:“王哥,你怎么来了,那只狗没有来抓我吧?”王叔让他先坐下,然后说那个监工报警了,明天是不能去上班了,他把一些我们的东西带来了给我们。
我看到了我的水杯和两件外套,同时还有许直叔的一把手套和给女儿买的书包,这个书包是许直叔昨天在路边摊看到的,他说他要买这个给兰妹上学,还未带回出租屋就发生了今天的这件事。
接着王叔说:“你们是江西的吧,我也是,我是赣州云城县的。下次进厂就先办一张假身份证吧,这里的很多厂子都瞧不起咱这种人。”
我问是因为这里的人很坏吗?他说不是这样的,各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好有坏,然后他让我们最近小心一些就走了。
这天晚上许直叔抱着那个书包睡着了,我则一夜都想回家。
连着几天我们都没出门,每天就煮一点饭吃,等过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去到了江边的一个工地。这里在做江堤,我和许直叔因为黝黑的皮肤和粗壮的身体很快就被选中了,这次我和许直叔不在一块干活,他负责和水泥,我则被安排到江堤上运土。
工地上有一座为工人们搭建的简易铁棚子,因为每天晚上可以不用上工,工人们则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许直叔还是和我睡在一间屋子内,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和那些人一起喝点酒呢?他说我们和那些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他。
五月的太阳十分毒辣,许直叔干活却十分卖力,按照那些人的说法——这家伙在和老天爷干架呢?每到晚上我给许直叔打水洗澡时,就能看到他那红灼的背和干裂的脖颈,同时他那本就全是老茧的手上的皮全都掉完了,每次他洗澡那疼痛的叫喊声让我感觉他不是在洗澡而是在受刑。
但是,工地是不是田地,这里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工头渐渐发现许直叔能够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可最后他只会要一个人的工钱。工头很聪明,在一个忙碌的下午宣布了水泥组裁人的消息,同时他还重点表扬了许直叔,那天晚上许直叔很是高兴,他让我买来了两瓶酒,同时还哼哼唧唧地唱了一首小曲。
睡前,他就着酒性他拉着我说:“咱们也是可以被人看得起的!”
可第二天,许直叔就被叫到了一个白色的大棚,那里是工头的办公地兼娱乐会所,出来后许直叔那一天都没有说话,而我则在等挖机掏泥时听其他人嘀咕说许直叔偷公款了,公款在我们的屋子他的床铺下被找到。
我知道这钱不可能是他偷的,我也顿时明白了那些无害的脸庞下隐藏的险恶与肮脏,好在钱不是很多,工头也同时决定相信许直叔一次,但之后我们也开始被彻底孤立。那些天,“土猪”“土狗”“滚回家”之类的话充斥在我们耳边,那些工人们,同时也是些苦命的人找到了他们对于我们的唯一优势,他们大多是本地的,他们能说当地的方言。
到了七月,气温已经很高了,我每天都求许直叔别那么拼命,可是他就是不搭理我,我只好常常给他送水和湿毛巾。好在初九那天下了大雨,堤坝上的工作都不能动,他终于能休息会了!
下午,雨慢慢小了,许直叔对我说咱不能忘了本,该回王庄看看。
于是我们举着从工头那借的小伞来到了王庄X所,这里一切如旧,我们也恍如隔世,觉得自己仿佛是刚刚才来到这座城市。屋主看到我们也很是热情,同时拉着我们进屋说她这全被人租了下来,她自己也成了守店的了,然后手指轻轻一拨弄就塞给了我们一张小卡片,卡片上的裸体女郎扭动着纤细的腰正妩媚地眨着眼。
我看到许直叔咽了咽口水,我想起他老婆已经出走三年多了。
许直叔说想看看之前住的屋子,在问完胖女人价格后对我说:“你想来一个吧?”
我说过年的时候我直接娶张舒滴,犯不着了。
他食指指着我然后笑了笑,我说我就在下面等你,接着他就上楼去了。
过了半小时,楼上响起了争吵声,我和胖女人都赶忙跑了上去。我看到还是在我之前和许直叔住的房子里许直叔正光着上身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大吵着,那女人捂着左脸,看来是被打了。
那女人一看到胖女人来了就一个箭步扑了上来,带着泪喊道:“这个死土猪打我啊,打我啊。”
许直叔也赶了上来说:“你还敢叫,老子和你说,再让我听一句‘土猪’试试。”
女人坐在地上,躲在胖女人身后,她本想再喊些什么,但是在看到许直叔那张举起的没有皮的手后,立刻就止住了声,随后便一个劲地哭个不停。
回去的路上,许直叔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他两只手左右摆弄着在向我复述他的光荣经历,他说那骚女人技术不行,一听到老子开口说话就骂老子是头莽干的土猪,还说要收我三倍的钱,看我不揍她个好的。
夜晚的城市像绽放的烟花,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景,说实话我常常会幻想,我是不是可以永远地在这个美丽的地方留下来,这座城市会接纳我吗?当我们穿过一处绿化地时,一团横亘在道路上方的小咬把我拉回了现实。我想和许直叔说绕一段路吧,可是他那突然变化了的愁眉的样子让我不敢开口,他低着头,用拳头抵住嘴巴,我就此停下,他则缓过神来看了看我,然后苦笑着说:“连那种婊子都瞧不起我。”
我拖着他的胳膊走回了工地上的小屋。
过了几天,他说兰妹快要报名读书了,他要回趟家。我们一起到工头那结了工资,工头听说他要回老家,忙问还回来吗?许直叔响亮地回答——来!我们一起去平价商场买了一些东西,我还特意给兰妹买了很多笔和本子,同时还买了几件衣服,我让许直叔把这些都带回去,然后给了他三千多块钱,让他转交给我的父母,之后我便在工地上一边做工一边等他回来。
八月底他回来了,我们都没有那种小电话,我是在工地上看到他的。那时我正在拖着一辆推车运着挖机刚刚从河岸边掏出来的泥,然后就看到许直叔拄着根木棍出现了。在他回家的这一个多月里我倍加思念他,我想他已经不单单只是我的二叔了,同时他也是我的精神动力,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个精神动力比任何时候都没有精神。
晚上七点下工后,我打了两份饭回到小屋,里面他用一条毯子盖着头躺在床上,那两只脚却突兀地张露了出来,我连声喊他没有动静,接着我问兰妹上学的事情怎样了?
我可怜的许直叔,他的脸上满是泪痕,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只知道在他老婆出走和他被人在厂子里打的时候他都没有哭。这条毯子在工地外那微弱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像碎裂的冰,他掀开被子后便开始号啕大哭:我是B型的,她却是A型的。我是B型的,她也应该是B型才对啊!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说入学要做健康诊察,在镇上医院抽血化验时我的许直叔惊讶地发现他女儿是A型血,可早在2004年国家废除粮食税并派一个乡村医生来为我们检查身体时,染纸上显示我、我爸和许直叔都是B型血。许直叔慌慌张张地又为兰妹核验了一下血型,同时自己也重新验了下血型,可最终还是一个B型一个A型。医院的护士看出他的焦虑,然后说孩子的血型也有可能是随母亲的,这给了他渺茫的希望,后来他带着兰妹做了亲子鉴定,结果仍旧表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于是当他提出要出去喝点酒时我立即就答应了。夜慢慢地深了,我俩坐在路边的小摊上点了两盘菜要了一箱酒,全程许直叔一个劲地喝酒,我看他举起酒瓶然后喉结便快速地一上一下动起来。他是个普通的可怜人,他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他一边吐一边喊,于是我知道了兰妹与他其实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事情。
我很愤恨,我很想拿起一把刀砍掉世界的万物,让它们都为许直叔哭泣,让它们比许直叔更惨。我看着头上的路灯不禁遐想,假设我娶了张石头家的女儿,而后她又为我生了一个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后我会怎么做?夜很深,它没有给我答案。
接下来我的命运则被推到了悬崖的边上。
一群青年,大概十五六岁,他们都染着奇异色彩的头发,两三人一伙各自骑着一辆电动车穿过马路来到我们的身旁。他们领头一人抽着烟,把烟吐成半个圈,然后对我说:“你们是谁家的小孩啊,还哭哭啼啼,要不要大爷给你们喂点水喝?”
我没有理他们,可是许直叔抱着路灯站了起来吞吞吐吐地对他喊道:“天底下就只有我一个大爷,你算哪根葱?”
接着那群人则都下了车,气焰嚣张跋扈。皓月当空照得天地大亮,这些人的身子拖着清晰的条条黑影,我拉着许直叔后退,那些人则更快地逼了上来:“两个孙子,叫几声爷爷我就饶了你们。”
许直叔当即挣脱我的束缚,身子一跃上前,酒瓶啪的一声砸在了那黄毛的头上。小摊老板闻声跑了出来,看了一眼就又急忙退了回去。接着他们十几个人则把许直叔围在道路边的垃圾桶旁,我焦急地看着他们用脚在踢着踩着许直叔,我大喊请人帮忙,可是没有人来理我。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没有手机报不了警,就算报了警,等到警察来的时候许直叔说不定已经被踢死了。我没有想太多,拿起小摊上抵住桌子的那块石头向最外围两人的后脑勺狠狠砸去,他二人一倒,所有人便都退开了,接着我来到许直叔的身边像母象护着小象一样提防着面前的这群狮子。
许直叔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了,我听着他声嘶力竭地喊着,不由自主地想低头看一下他的伤,可接着我就被人从身后踹倒了,随后密集的拳脚便都砸到了我的身上。
二十多分钟后,我被他们架在电动车上扔到了郊区道路中心的花坛里,我扯着几束花费力地想:许直叔能回到小屋里去吗?
法庭上审判我的所有人都很激愤,他们说我罪大恶极,说我不配为人,说我害的其实是两个苦命的家庭。原告律师这样说我时我笑了笑,他立即觉得我是在向他挑战,于是他的声音和语言则直接奔向了粗鲁。我对这些不在意,唯一让我在法庭上心灵为之一动的是我在转身被特警带走时,我看到后面的听审席上许直叔正凝神地看着我。我顿时泪流满面,我哭了,我在我快到而立之年的时候从法院哭回了监狱。
来到监狱后,我被放入到了G组,这里的犯人都很朴实,有一个人的年龄和许直叔是同年,我时常望着他,把他想成是我的许直叔。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回忆一下这六七个月以来的生活,每当凌晨深夜,我躺在狱舍的木床上,许直叔鹤立鸡群站在众人之中并大骂那个监工的样子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许直叔是一个英雄,他不仅是我的榜样、我的骄傲,同时也是我头上那颗不可触摸的星星。
我想,要是我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那我一定不会选择出来——对呀,为什么要出来,我为什么要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不同的命运?
躲在山里?缩在沟里?逃入泥里?就算是的话又能怎样呢,坐在自家的石头台阶上,看夕阳慢慢地落下,天空由金黄变得粉嫩,入夜的大山里猫头鹰时而飞过发出一阵低鸣,我拿起小蒲扇,摇啊摇,慢慢地消失在黑夜里。
黑夜,乡里的黑夜比城中的阳光给我更多的温暖……
但又或许一个人不会同时拥有成长和对成长的感悟,如果我不出来的话,我就不会渴望家乡,如果不离开许直叔,我就不会希求他的存在。
我之前听工地上的女财务说,工头刘总就让人给他做过传,里面的成就可以比肩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我想我也应该为许直叔做个传,虽然他没当过皇帝,但是他值得,希望我初中水平的文字能够把许直叔的故事说清楚。
几十天前的一天下午万里无云,监狱长找我聊天,他让人把我叫到审讯室,我在那等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快到饭点时他带着笑也带着酒出现了。我和他说我戒酒了,他点点头,说戒酒好,喝酒误事,问我在这里过得还习惯吗,还有啥想做的。
我说能不能让我见一下我爸妈。
过了一个多月我就看到了那衣衫褴褛的母亲,再过了一天,也就是今天——11月中的第14天,他又带上了一瓶酒,这次的酒应该要高级些,虽然我不知道 “剑南春”是什么等级,但是光看它外形上的包装我就能知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二锅头了。
这次我依旧说不喝酒,但他却还是让人拿了个碗给我满满地倒了一碗,我感觉他今天有些高兴,他说:“许海啊,你不要担心,你的罪过我已经全面又全面地了解了,你杀了人,按照法律和道德律,你应该被判处死刑。”
我木讷地看着他,对他说的话不置可否。
他嘴巴轻轻地张了张,好像有些难为情,之后看了看他旁边的警卫员,再看看我,接着头一沉恶狠狠地喊:“你啊,残害社会,连人都敢杀,可以说是早就该死了。但是现在你有了一个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北京xx部王xx的夫人患上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才能救命,可你说巧不巧,她的骨髓大半个中国都没配上,没想到让你给撞到了这个好运。”
整个审讯室里的警卫都笑了,我感觉自己也该笑一下,但是我没有,我说道:“所以呢?”
“所以呢,所以你马上就能到北京去接受死刑了,嘿嘿。”这个监狱长春光满面,肚子也好像慢悠悠地涨了起来,“今天你就不要戒酒了,我已经向阎王爷求了情,他老人家说你死前做了件好事,可让你喝一点。”
大约一分多钟后,审讯室的灯闪了一下,传出如同在空洞的树林深处某根枝条折断的“啪”声。监狱长有些发怵,小脑袋一顿一顿地转着,看来阎王爷真的显迹了,于是我就用这灯光当做小菜,把眼前的酒一饮而尽。
呼——看完这本“《理想国》”后我便把不自觉塞着的那口气全都舒陈了出来,我看了看桌前的闹钟,显示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台灯滋滋地响着,我转身看了下王民繁,他正侧着身沉沉地睡着。
时间奔流而过,可这本书我依旧留着,它能够让我如同亲历般地体会到这个有着巨大参差的社会,让我在一个模糊的年龄摸到真实可触的藤蔓,从而能够再度以仿佛乍见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在我拿到这本传记的五天后,政委便组织所有人开了一次教育会。那时我坐在桌角,眼神茫然地看着面前的瓷杯,那里——遥远的西半球,一股股热气穿过层层密布的茶叶飘向空中。渐渐的,我有点昏沉,夜晚的灯仿佛在变戏法,它一下进入到我的视线中,一下又消失不见。心中烦了,我推了下旁边的民繁,小声说道:“民繁,什么时候散会啊?”
“陈哥,我看还早着呢,你刚才没听吗,政委说咱送到省城的那批犯人里有个人在路上咬舌自尽了,这件事连北京里的一些人都惊动了。”
我呆了一会,眼前仿佛闪出了一个人踏马奔向远方的画面。临行前他回头问我远方到底有多远?我不知道,没办法给他答案,但我伸出手,请求他带我一起走。
突然政委手里夹着的烟炸出了火星,这一下就把我拉回了现实,许多人跑上前,会议室里顿时乱成一团——可外面还是清淼无虞的。我对着窗帘后的黑夜小声说:“这就是一件小事罢了!”
如今我已经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小主任了,我主动向上级请求负责乡村的工作,同时我也常常自费向城乡经济股的马主任送礼,他每次都说不必这样,但是每到逢年过节时我还是送礼给他。
去年中秋那天,他终于忍不住了:“老陈,你这到底是干什么,你就直说到底是不是检察院让你来套我的话……”。
我把他拉回到沙发上,然后给自己甩了一个巴掌。
他抹了一把脸,诧异地盯着我,同时眼镜片下的两只眼珠正奋力地向我这跑着。
今年的春天我下乡调研,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伯问我他儿子想出去务工,能不能给个推荐?我顿时就想到了那本遗传,于是我问:“为什么不能留在乡里做事?”那个老汉笑着说:“年轻人嘛,就是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那些好地方。咱也希望他能有出息,不要像我一样永远待在这个山沟沟里。”
万物复苏,春回大地,水库上的冰都化开了,我说:“让我见见他吧!”